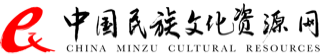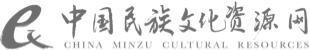昌都卡若遗址
昌都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市昌都以南12公里的卡若区卡若村,在澜沧江以西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与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址共同被称作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
关于卡若遗址的发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曾亲自参加过遗址发掘的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侯石柱撰文写到:1977年,西藏昌都水泥厂放映了一部名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银幕上一些出土文物的镜头引起了看电影的水泥厂工人们的注意,他们联想到不久前水泥厂因扩建厂房,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许多破碎的陶片、石片等,和电影上的出土文物很相似。因此他们将捡到的碎片送至昌都地区文化局鉴定,经恰到昌都征集文物的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仁青、索朗旺堆、欧朝贵3名文物干部的观察鉴定,初步确认其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4]。由此逐步拉开了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
197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揭露面积230平方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了卡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两次总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通过对两次发掘成果的研究保护,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
通过三次考古发掘和一系列的研究,考古学界逐渐明晰了卡若遗址的年代与分期。木金最早委婉表达分成两期并不合理;王仁湘经过研究,大概将之界定在距今4300~5300年之间,延续1000多年,分为3个时段;石应平在分析了卡若遗址地层关系及碳14年代测定数据之后,也提出可将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早期的年代范围约在距今5300年前或更早;中期约在距今5300-4400年之间;晚期约在距今4400—4200年之间,前后至少长达1100-1200年左右”[1]。不同时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化显示了文化上剧烈的变化,霍巍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卡若遗址的跨度本来就比较长,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由于高原的生态环境发生过剧烈的变化,需要从考古学上去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环境问题。
关于卡若遗址的动植物以及生业方式[3],童恩正、冷键、索朗旺堆、霍巍 、石应平等人通过出土地工具和粮食、动物骨骼等认为“卡若文化” 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粟米为主要的种植作物,饲养猪等家畜,还存在狩猎野生动物的现象。
关于卡若遗址的居民族群,现在并不能直接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方式分析,而是通过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学者们存在几种观点。一是土著说,二是迁徙说,三是相互影响说。部分学者认为卡若遗址的居民就是世代生活在西藏的居民。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青藏高原高寒不适合人类生存繁衍,因此是黄河上游等地迁徙而来。因为学者们在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类石核上剥下的细长石叶,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当中。童恩正还指出,卡若文化可能与黄河上游文化是同源,也可能是相互影响[1 ]。
卡若遗址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变化,从半地穴到地面,再到木架、雕房式[2],人类生活起居的环境越来越适合生存,同时对于建筑材料的利用也出现的了更多选择,需要更加集中的人力物力。同时,在今天藏羌彝走廊内的建筑之上也可以看见卡若遗址建筑的部分影子。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卡若遗址对现在走廊内民族文化的影响[6],以及走廊内多元文化的共生、交融历史源远流长。
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奠定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开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至少在距今5000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时间里,西藏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些先民与中原地区的人们在文化上存在相似或者联系。1979年8月18日,卡若遗址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卡若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研究、保护的同时,我国对卡若遗址也进行了适当的开发,规划为遗址公园,供人们参观和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
作者:未沫
参考文献:
- 霍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J],中国藏学,2010年。
- 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J],西藏研究,1982年。
- 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J],四川文物,2007年。
-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页。
-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79年。
- 叶志强:《从考古遗迹看羌文化对藏彝走廊的影响》[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